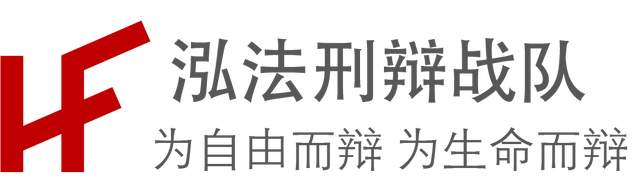关于律师
案例证明实力,给你信心的保障
原创 洪树涌、陈为 广东泓法刑辩战队
去年写《刑事辩护中的“心证”》时,就有朋友打趣,又是“白纸裁”,又是“影响心证”,看来多年的辩论瘾还没过够。
上次写《刑事辩护的“赢”》,又有朋友说,又是“拆地基”,又是“建房子”,鉴定为评辩论赛后遗症。
当然,很多辩论上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于法庭辩论,所以严格意义上你要说刑事辩护像辩论赛,其实是因果倒置的。而我也是毋庸置疑地认为——打辩论与刑辩,在我看来本就是一套范式的两种表达。
而我想,人在构建新领域的认知体系时,若能从旧经验里借一把梯子,总是好过徒手攀岩。
而在这些旧经验里我借的第一把梯子,应该是“举证责任”。

01
辩论赛,是真空状态的“公平竞技”
任何议题的讨论中,正方天然背负着“立论”的举证责任。而反方一般来说义务会更轻些——即便只做拆解,不做建构,只要正方对于立论的举证责任没有举证到位,那理论上都是反方赢。
也正是由于“谁提出,谁举证”这一规则天然偏向于反方,所以许多辩题会尽量给双方赋以尽量相近的论证义务,以避免让反方只是纯靠反驳就能拿下胜利,特别是诸如“我国应/不应该征收遗产税”这类政策类辩题,反方不可能只需要等正方来论证改变现状的利好,评委也会要求反方也要给出一套维持现状的利好来形成相抗。
也正由此,在辩论赛中,当每有一群新人刚开始打辩论赛,问出“到底一场辩论赛怎么样算是赢”的问题时,我们往往会给出这么一套比喻:打比赛就像是“建房子”,正反方各自通过立论构建一套房子,而双方通过一场比赛的攻防来互相“拆房子”,在比赛结束后,谁剩下的房子更完整(核心论点留存更多),谁就是比赛的赢家。

02
刑事辩护,更侧重举证责任的合理承揽
刑事辩护,与比赛最大的区别就是,比赛输了不会多坐几年牢。
这不是玩笑话,输赢后果的严重性确实会影响举证责任的承揽。
当脱离了辩论赛这种真空状态的“公平竞技”游戏,当你面对的是“举证不力就得承担不利后果”的时候,我们自然需要对举证责任有更合理的审视。
比如我的《刑事辩护中的“心证”》中聊到的诈骗案,其实就是对处于天然正方的检察院的举证责任的合理承揽——如果检察院还未全面了解案件事实,那我们作为辩护人,可以先帮助检察官从侧面先了解一些;如果检察官对于案件的定性与解决途径尚有疑问,我们可以去主动提出我们能够给出的解决方案。
对于举证责任的合理承揽,非常适合且有利于存疑案件初期的辩护工作。比如说审查批捕期,检察院还并不是完全处于正方的地位,其对于是否批捕是有着决定权的,如果你指望着检方充当正方,来完成、完整其应当有的举证义务,那无疑是把命运完全地交到了对方手中;而只有辩护人和当事人反应过来,我们应当向每个阶段的“裁判者”尽可能地展示我们对于举证责任的合理承揽时,我们才有可能尽量在每个阶段拥有尽可能地主动权。
再比如我曾经指导过另一个职务侵占案的当事人,我的辩护思路是一来其不构成职务侵占的构罪要件,二来其与公司的合作模式是合法合规的。在描述其合作模式的过程中,我们做了相当详尽的说理论证,当事人也曾不解问过我们,按道理来说不是应该“谁主张谁举证”吗,为何我们作为辩护方反而要做这么多的自证工作?

当然我没有说什么举证责任的合理承揽,我只是说,有些事,如果你相信做在前头、由自己来经手是更可靠些的,那就不要只是被动等待。
因为辩护工作不是真空状态的“公平竞技”,辩护本身就是需要你在原本就倾斜向另一侧的证据天秤上用力加码,天秤才更有可能向你倾斜。
辩论赛的胜负结束后,双方可以握手言和,评委也能笑着复盘“刚才那招拆得漂亮”。但刑事辩护没有“赛后”——当法槌落下时,有人要踏入高墙,有人要背着案底走过余生。
这些年我越发觉得,刑辩律师的战场,从来不止于拆解对方的逻辑。那些从辩论场上借来的“胜负手”,终要落地为一场更沉重的建构:在检方的“证据大厦”旁另起一座危楼,在法官的“心证天平”上投下一粒硌脚的沙,在看似铁板一块的指控里,凿出一道容得下“另一种可能”的裂缝。
毕竟我想,司法的尊严从不在于盖棺定论的速度,
而在于允许所有“为什么”在尘埃落定前,
都有资格站在光里。
(完)
律师简介 / Lawyer profile
洪树涌 广信君达高级合伙人、管委会委员、刑事诉讼专业部部长、广信君达泓法刑辩战队负责人
陈为 广信君达律师、广东泓法刑辩战队核心成员、广州市律师协会辩论团成员

广信君达泓法刑辩律师战队——